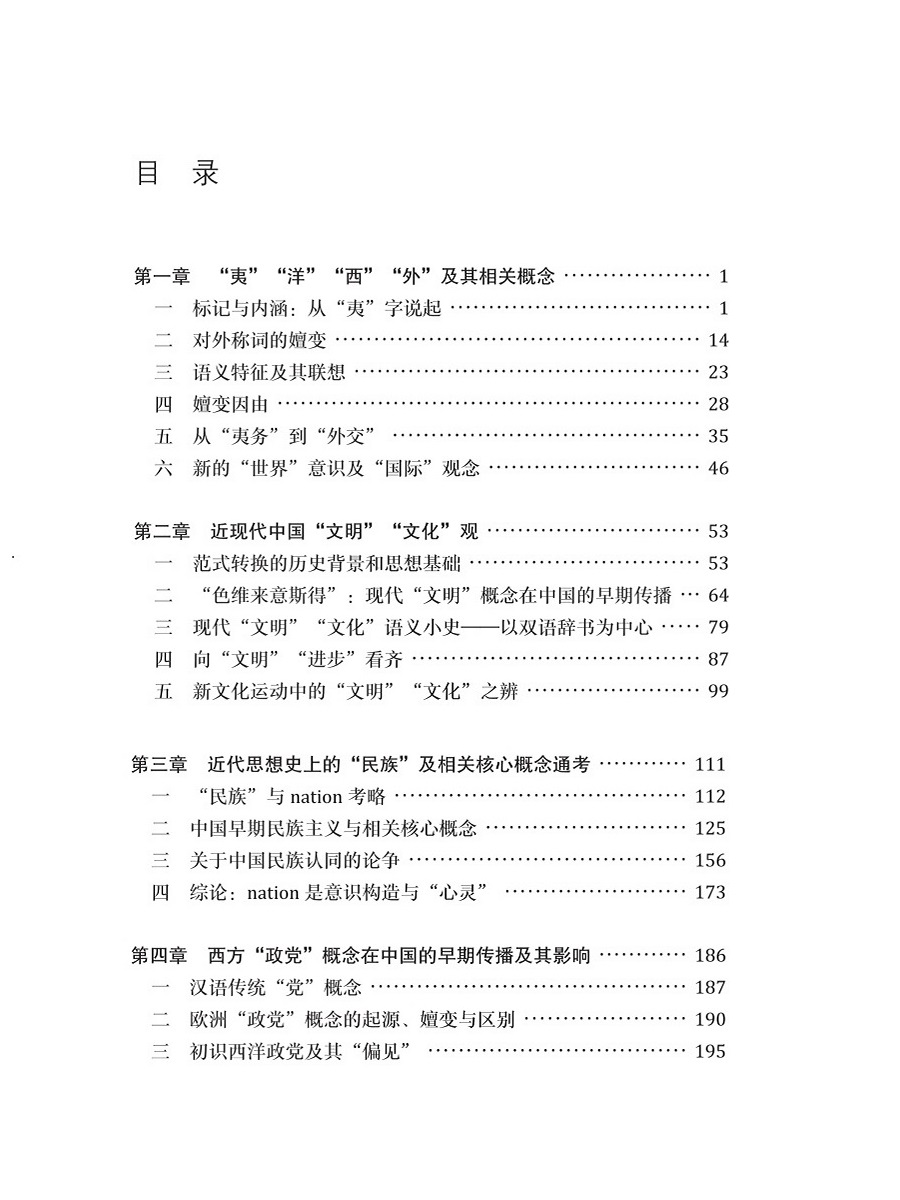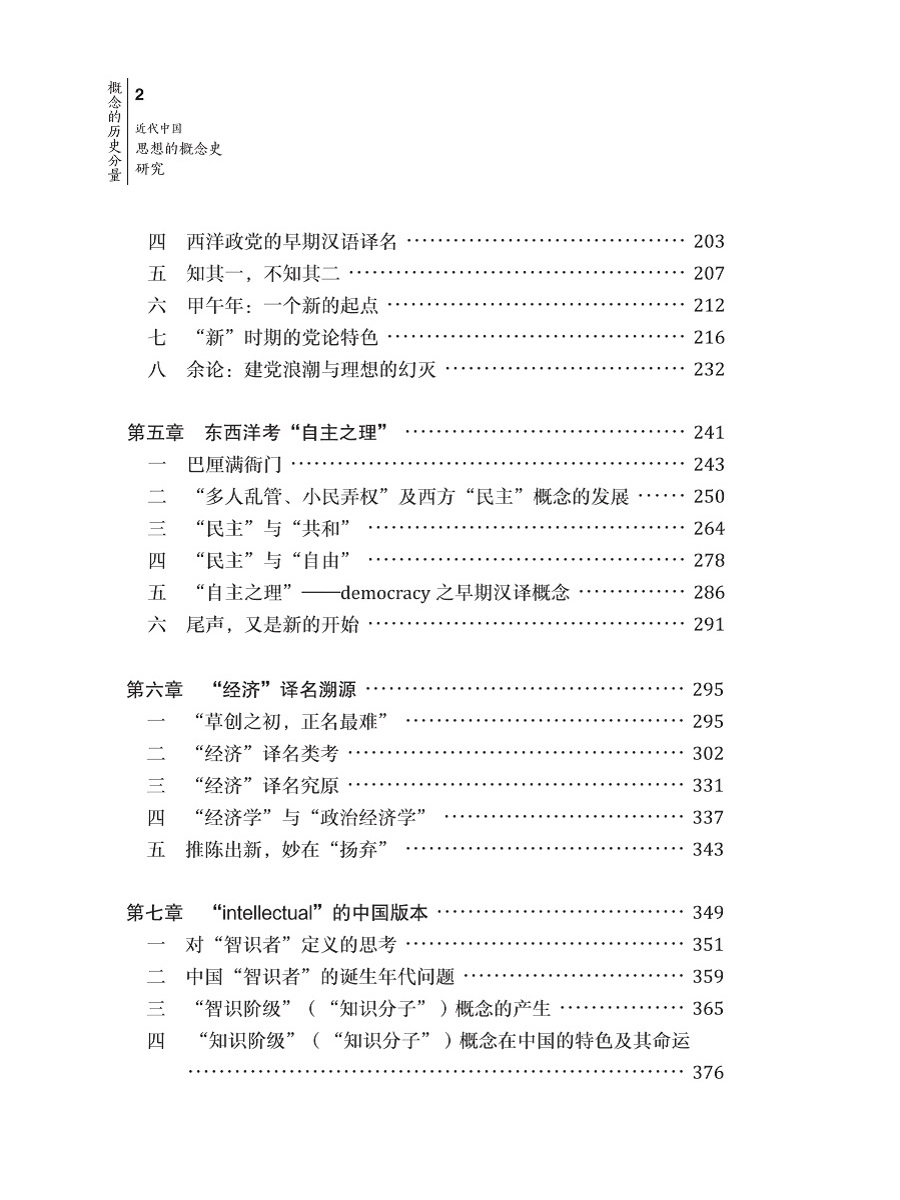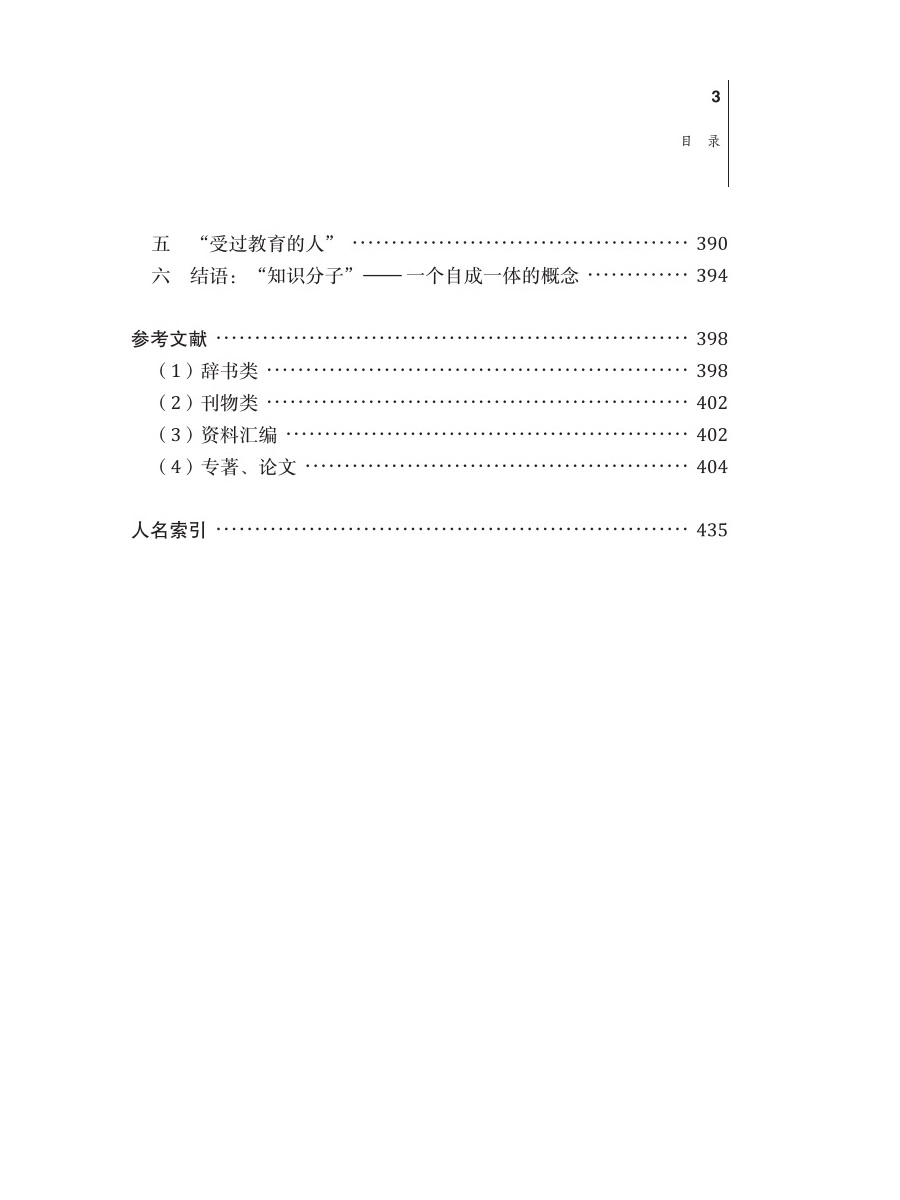方维规《概念的历史分量:近代中国思想的概念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8+445页。
发布时间: 2019-04-18
方维规著《概念的历史分量:近代中国思想的概念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8+445页。 序 言 最近几年,总有朋友在不同场合问起我的概念史研究近况。我说自己还在不断打磨和拓展过去的研究。如今,经过三年的时间,这项工作基本完成。面对眼前这部即将付梓的书稿,抚今追昔,感怀良多。如此表达此刻的心情,绝无渲染夸饰之意。屈指算来,从我最初从事概念史研究到现在,已经过去二十年多了。回顾这段学术生涯,当然不止是自我感怀,同时也关联着概念史进入中国的历程。 不妨先从一个插曲说起。多年以来,不少学者和学生第一次听说我在文学系任职,不免有些惊讶。的确,2006年回国前,我先后在德国多所大学的语言文学专业教书;回国后,任教于新澳门新葡萄娱乐。后来才明白,他们很早就读过我的概念史论文,按照学术分科的惯例,便以为我必定是在历史系任教。然而回想起来,当初从文学研究转到概念史研究,既是个人精神探求的方向使然,也与特定时间的学术机缘有关。 想当初,我于1987年从东德洪堡大学转赴西德留学,追随当代欧洲形象学之父狄泽林克学习比较文学。在我主修的三门课中,有一门是“语文学”。许多人知道,语文学侧重从文献的角度研究语言文学问题,乃西方学术传统之根基。通过这门课程,我了解了欧洲语言与历史文献的基本脉络和方法论,增强了理解语汇概念的学术敏感性。当时我并不知道,这门课程会奠定自己后来选择概念史的知识感觉。 1992年,我以探讨“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随后在特里尔大学开始教授论文的写作,沿着形象学的方向,转向关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自我形象”。随着研究的深入,我逐渐感觉到,无论是他者形象还是自我形象研究,最终都会触及认知形构背后的观念因素。换言之,概念是思想的出口、情感的内核。如果不对制约形象认知的概念形式进行深入探究,那么,这种从文学出发的研究便可能遭遇深层的困惑。然而,当时这些思考只是尚未明确的学术感觉。不久,在我初步完成教授论文后,出现了转向概念史研究的契机。 1996年,我受聘担任哥廷根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参与一个颇具规模的跨区域研究项目:“近现代汉语学术用语研究”。这是我从事概念史研究的起点。这个项目提供了许多与欧美和中国的一流学者交流的机会,对此后的学界进展影响深远。电脑在彼时中国尚未普及,而在德国,已经开始运用数据库开展学术研究。项目组占有不少国内学者当时不易获得的历史文献,并将之转化为数据库资源。通过阅读、整理和考证这些近代文献,我对概念史产生了浓厚兴趣。而此前形象学研究中遭遇的困惑,也因此获得了方法与视野更新的可能。也是在哥廷根期间,我有幸旁听了马普历史研究所召开的“哥廷根史学对话”国际研讨会,尤其是概念史头号人物科塞雷克的演讲,很是让人兴奋。 在这个阶段研究的基础上,我撰写了第一篇概念史论文,阐释近现代中国“文明”“文化”概念的嬗变。这篇论文的写作,并非仅仅是对“文明”“文化”概念的史料收集与整理,而是有效运用了德国概念史研究提供的方法论视野。对于这种学术方法,当时国内学术界鲜有了解,更不用说运用于近代史领域。这项研究在中国发表以后,受到很多学者的关注。对我来说,通过这一借鉴德国概念史进行实证研究的较早尝试,不仅意识到概念史方法的重要性,而且发现这种方法对于拓展近代史研究视野的意义。 在我的观察中,除了少数通史著作之外,很多近代史论述往往集中在某一相对狭窄的时段。有了概念史眼光,便可以更好地在长时段里看到一个社会变化的总体特征。而由此理解概念的历史内涵,不可避免会遇到翻译问题。很多学者都清楚,这是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核心问题。但对此的理解,一方面必须对相关概念在西方传统中的演进过程有清晰明确的历史把握,另一方面需要将之回置到近代中国的长时段语境中,理解其容受与更迭的嬗变过程。显然,要做到这两个方面并非易事。而我当时之所以决定置身概念史研究,是考虑到自身的学术准备中,多少有一些语言理解的优势,又在如何精准把握史料方面做过一些努力。只要假以时日,便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拓展对近代史学界有所启示的学术领域。 完成“文明”“文化”问题研究之后,我逐渐发现,对于近代思想问题的理解,必须将之置于一个概念群或意义群中展开。换言之,近代国人对于很多新生观念的理解,依赖于不同概念或意义构成的结构性关系。比如:对于“民主”的理解,就必须将之置于“议会”“民主”“共和”“自由”等语汇形成的概念集群。而对于“经济”的考究,则需要深究其背后“政治”与“经济”两种意义的历史构造关系。至于对“民族”的把握,则必须勾稽“nation”一词多译所形成的复杂意义网络。这些思考构成了我此后几年研究的基本线索。而两篇概念史文章先后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对我来说无疑是一种鞭策。 2006年回国后,我开始直接参与中国学术界的思想讨论。一些关注概念史研究的学者不时跟我联系,想了解理论方法层面的问题。我慢慢意识到,概念史研究已经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但不少人苦于找不到方法门径。为此,我暂时放下对近代思想中关键概念的研究,从2006年开始,连续写了四篇理论文章,介绍德国概念史的方法:《历史语义学与概念史:关于定义和方法以及相关问题的若干思考》,《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兼谈中国相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鞍形期”与概念史——兼论东亚转型期概念研究》,《概念史研究八论:一门显学的理论与实践及其争议与影响》,另外还在一些书评中说及理论。这些理论文章在学术界引起不小反响,不少人或许借助这些文章了解了概念史研究的基本方法论。 出于教学研究以及个人学术兴趣,我同时介入文学社会学和海外汉学研究领域,从概念考辨和脉络梳理出发,写了一些论文,旨在正本清源。这些零散文章或许也能折射出,概念史始终是我最钟情的领域。完成上述理论文章之后,我开始考虑以更为整体的方式理解近代思想的结构性问题。事实上,通过概念史视野进入这些历史问题,最大的挑战在于,那些影响西方的重大概念,是否也在近代中国具有同样重要的社会形塑和人心再造的力量?因此,必须以结构性的眼光来理解近代历史演进的内在脉络,并以此来审视这些概念在其中的意义位置。 基于上述问题意识的更新和深化,我重新整理并拓展原有的关键概念研究,将之回置到历史演进的结构性位置,进而探究有待进一步考辨的其他相关概念。比如:“夷”“洋”“西”“外”作为近代涉外语汇的因应与变化关系,“政党”在近代的翻译和理解问题,等等。从这样的思考视野出发,经过这些年的反复推敲和深入开掘,最终形成了这部概念史论著的结构框架。 在我们的历史常识中,近代思想变革的前提是晚清士大夫理解西方眼光的变化。“夷”“洋”“西”“外”,这些语汇早已成为近代历史研究的基本概念,而对每个语汇背后对应的时代契机、观念脉络及其相互关系,很少有人开展深入的历史查考。实际上,没有“夷”“洋”“西”“外”之递嬗,即“夷夏”之辨向“国际”话语的转型,许多产生于近代、与外部世界和事务有关的新概念是不可想象的。一旦脱开这种概念考辨工作,我们认识近代历史的眼光很可能会变成空洞而混乱的观念杂合。因此,本书第一章首先探究这些涉外语汇在19世纪时空变迁中的演进脉络(初稿为1997年在哥廷根召开的一次国际研讨会上发表的英语文章)。在这一变化过程中,近代有识之士审视西方的方式发生了思想突变,也就是首先涉及“文明”观念的文化价值大转换,认识中国在人类历史演进中的位置。第二章便集中考证“文明”“文化”概念嬗变背后之自我理解范式的革命性转变。深究起来,这种精神坐标的改变和价值的转换,最终落实为对中国作为“国”之身份的再定位,也就是透过“民族”亦即“国族”(nation)这一概念范畴,重新审视个人、群体与国家的内在关系。显然,“民族”并非孤立的概念表征,它包含一个核心概念群,诸如“族类”“人种”“国民”等。对这些概念之发展和变化的深入探讨,构成第三章写作的主要内容。 从上述以“民族”为中心的认识变革,近代知识人面对国家的道德责任感,迫切需要找到新的组织依托形式。而西方“政党”概念的传入,使得他们得以将松散的个体行动转为高度组织化的群体实践,并由此缔造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根基。第四章内容围绕西方“政党”概念的译介与汉语现代政党概念的起源、发展阶段及其确立,梳理政党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中发挥的决定性形塑力量。晚清人物对政党概念的探索,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一个重要侧面。不过,“政党”概念的传入并非孤立的思想事件,与之高度相关的“议会”“民主”“共和”“自由”等西方概念在中国的译介与阐释,在近现代中国新的政治场域中引发不同的观念迭变和思想纷争,最终导致民主观念的飞跃。换言之,如何确立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政治形式,成为知识人的紧要关切。第五章主要梳理“民主”等概念在中国的译释、嬗变及其运用,以及体现知识人之关切的不同意义表达形式所呈现的政治面向及其结构变化。当然,政治形式并非近代中国唯一的迫切诉求;积贫积弱的现实,同样要求“经济”眼光的重构。而这种重构的契机,与时人对西方现代 economy(economics)的许多汉语译名难解难分。论说现代“经济”概念时的大量选词,或明或暗地切合于西语 economics。而作为“经世济民”的简称,“经济”原本是西方“政治经济学”概念的汉语译名。正是通过各种意义纷争,“经济”获得了新的政治视野和价值取向。查考 economy(economics)汉语译名的来源和类别,探究“经济”一词的本原与蜕变,以及对不同译词来龙去脉的分析,一方面可以看到西学东渐的一个精彩场景,另一方面则从概念史的特定视角展示中国近现代经济思想史的一个侧影。这些考辨即为第六章的主要内容。 若说近代思想中的关键概念的因革与迭变,与19世纪中后期士大夫与传教士的努力和传播关系密切,那么,随着新的观念进入20世纪的思想场域,深化接受与传播的历史使命,逐渐凝聚在试图为中国未来担负责任的知识群体身上。这便是起始于20世纪初期,并于1920年代扮演关键角色的现代“知识分子”。而要理解这种身份的历史型构过程,就必须追溯“intellectual”这个西方概念在中国的命运,即“知识分子”这个颇富中国特色、自成一体的概念之起源、发展、运用及其思想意味。正是这一群体,成功改变了近现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面貌。这便是最后一章处理这一问题的深层原因所在。 过渡社会的显著特征,是各种经验以及与之相关的阐释模式和表达形式之加速的、充满危机的急变。伴随着传统经验模式的转型,需要新的表达形式来阐发剧变,以确切地呈现经验变化。对经验阐释来说,语言表述无疑具有根本意义。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进入一个独特而漫长的过渡时期,由传统过渡到现代。这一历史过渡时期的概念史,自然也是现代化之经验史。语言因此而在诠释这个时期加速的经验变迁时获得新的分量,传统概念因为新的含义关联而被融入全新的经验空间。此时,词语史只是一种进入途径,我们则要透过词语发现其重要的政治和社会蕴含,以及词语所表达的相关经验和思想。 就德国亦即欧洲的概念史而言,科塞雷克在1996年的一次对谈中指出,作为方法的概念史当为解读现代化做出贡献。他一直试图以四个范畴来界定历史过渡时期的概念史,即语言的民主化、政治化、可意识形态化和概念内涵的时代化,并在具体研究中测验这四个向度。概念史不能没有自己的理论。如果以为概念史除了挖掘史料而别无他求,那会很荒唐。科塞雷克晚期理论探讨中的概念史观点简要而鲜明,如他在《概念史:政治社会用语的语义和语用研究》(2006)一书中所说的那样:与所有史论一样,概念史也需要假设,没有假设便无论点可言。纯粹的史料堆积绝非概念史,关键是把握概念网络中的大概念、下属概念、对立概念等各种概念之间的关系,以揭示概念的内在语义结构。惟其如此,才能彰显一些特定概念的建构能量,否则无法真正理解文本和语境。 的确,真正的概念史从来不只是概念的历史。根究概念嬗变而外,更在于提炼历史语义的内在结构;除了透过语境来理解文本,更重要的是考证和解析那些富有“整合力”的特定概念。这就是本书取名《概念的历史分量》的用意所在。本书对中国近现代史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即“大概念”的探究,很大程度上也出于这一思考。概念史的主要特色之一,就是挖掘那些弃之则无法经验的概念,或曰不可替代的基本概念(科塞雷克语)。 最后,我还想说一下前文已经稍有提示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西学东渐亦即知识传输中的翻译问题。还是在1996年的那次对谈中,科塞雷克论及翻译和概念史的关系:在他看来,德语概念史很可能从翻译的必要性中获得极大推动。作为科学母语的拉丁语退出之后,诸多西方语言自然而然的将拉丁语融入各自的民族语言。这在意大利发生于但丁时代,同样也很顺利的发生在法国和英国。而在德意志土地上,人们总体上不得不另造新词,或通过借词来对应拉丁语词汇,用以丰富自己的语言。要在德语中理解陌生的拉丁语汇,需要极强的感受力和理解力。翻译和对拉丁外来语的容受,自然要比直接采纳拉丁语难得多。再看斯拉夫语,它对拉丁语的翻译则更为困难。科氏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来说欧洲语言的发展:经过艰难跋涉,从宗教改革时期的语言到19世纪各种革命时期的语言,确实克服了无数崇山峻岭,语言库存完全变了样。 现代汉语尤其是学术用语的很多重要词汇和概念,均产生于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或在这个时期推陈出新。“西学”的译介极大地丰富了汉语学术用语。歌德曾说,一种语言的威力不在于拒绝外来语言,而是化为己有。上文说到历史上欧洲语言之间的化为己有,常常是费难之事;汉语和西语这两类迥异的语言之间的翻译,当然更是难上加难。从西方到东方,岂止是崇山峻岭,那是千山万水,走过艰辛的翻译路程。那些知难而上者不仅需要感受力和理解力,还需要创造力,翻译过程无疑也是创造过程。哪怕如严复对待译事那样“一名之立,旬月踟躇”,也未必译有所成;易言之,这里往往不只关乎译事本身,甚至连接几代人对某个概念的认识和发展过程。本书所探讨的绝大部分概念,均为“翻译”概念。即便是不属于翻译范畴的“夷”“洋”“西”“外”之新旧递嬗,亦同许多西方(新)概念的中文翻译密切相关。翻译不只是言语形式间的相互转换或曰符号转换,而是理解和阐释;尤其是文化、社会、政治概念之翻译,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思想之传导,即对外语概念及其思想的领会及其在汉语中的传会。这也都是本书着重讨论的问题。 中国人有十年磨一剑的说法。我想,这本书作为二十年研究的心得,若能对中国近现代史的思想深化与视野拓展有所助益,也就达致初衷了。 方维规